《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谈》(一)
2020-11-02

2020年11月2日下午两点,本次“上美讲堂”有幸请到了张晓凌老师主讲《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谈》。
这个问题是当代美术的重要命题之一,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大家之所以觉得这个题目有点老,是偏见造成的,理由我下面会讲。近些年,我参与了“中华文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等项目的筹划与评审,对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规律有点粗浅的认识,对其成败得失亦有些许感悟,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探讨。正如你们所熟知的,所谓“重大题材创作”,即西方艺术史上的“历史画”,也是中国艺术史上的“故实画”。所以,今天的讲座中,这几个概念是因其同义而混用的。讲座共分四个版块,即“重大美术题材创作现象与问题”“何为历史画”“历史画的创作实践”“历史画创作的风格与形态”。

一.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现象与问题
在一个崇尚“自我表现”或“自我表演”的时代,为什么要谈论由“历史”“国家”“民族”“重大题材”“史诗”这些大词组合起来的宏大叙事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列举两个现象就可以回答。第一个现象,近15年来,中国掀起了一个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新浪潮。这其中包括2005年文化部主持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2年中国文联主持的“中华文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2013年中国国家画院主持的“丝绸之路美术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等五、六个国家级的美术创作工程,至于省市级的就更多了,我将之称为“超级文化现象”;同时,在欧美当代艺术领域,重大题材借当代艺术形式而转世重生。我们知道,西方美术迈入现代是以和“历史画”的解约为前提的。换句话讲,现代主义艺术为“历史画”撰写了墓志铭。然而,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沉默,重大题材穿越形式主义、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迷雾,还魂般地在当代艺术中重现。在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的现场,我们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它重返现场所带来的震撼。基于这种感受,我将重大题材创作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这也是重大题材创作的四种形态:古典写实主义阶段、现实主义阶段、现代主义阶段、当代艺术阶段。这个问题,我下面再细谈。顺便插一句,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为什么outdated,原因很简单,用的是当代艺术形态,意识却还停留在现代主义、形式主义阶段。
东西方当代艺术领域同时出现“重大题材”创作热潮,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论“宏大叙事”的理由。

美术界一直流行一个说法: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得好。果真如此吗?画“开国大典”与画瓶瓶罐罐是一个等级的吗?我想再次强调:题材是很重要的。这方面,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前些年,我曾去梵蒂冈观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进入《创世纪》《末日的审判》厅时,身心一下子悬空了,灵魂出窍般地进入画面,开始了从“创世”到“末日”的精神漫游。迎面而来的,忽而是创世的奇迹、力量与盛大景观,忽而是末日的绝望、哀嚎与救赎。它们彼此纠缠在一起,让漫游者的灵魂在惊心动魄的叙事中,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洗礼。在知识层面上,这两件作品是“神话”,而在精神层面上,它们却是无与伦比的“真实”。出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欧洲的博物馆,大多是精神的道场。他们的少年儿童精神与性格的养成,以及文化认同感,是从博物馆的读画中开始的。在俄罗斯的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威尼斯艺术学院美术馆等,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认真读画的情景。面对这样动人的场景,我切身感受到:在当下,重大题材创作(历史画)仍以其巨大的精神含量和崇高的美学形式,穿越时间来滋养当代人的心灵与精神。这一点,无论是塞尚的“苹果”,还是杜尚的“小便池”,都是无法做到的。
虽然重大题材创作的当代意义不容置疑,但中国的几项创作工程却一直伴随着质疑与批评的声音。我将各类问题概括为五个方面:
1、当代中国需不需要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2、何为“重大题材创作”?如何在理解重大题材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将史实转化为史诗?
3、如何认知历史并确立创作文本?
4、当代美术家有无能力担纲重大题材创作?
5、重大题材创作有无可能借助题材的力量而完成美学风格及艺术形态的创新?

当代中国需不需要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我私下里听到不少这方面的质疑,质疑者的理由有二:后结构主义以来,所有的宏大叙事因其意识形态含义所以是有毒的;现当代艺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因而是反宏大叙事的。在我看来,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既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有悖于世界当代艺术发展的现状与事实。后一点,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这些年,在西方获奖的当代艺术作品都是“重大题材创作”。至于中国需不需要重大题材创作,我的看法是,这不是由某些批评家、艺术家说了算的,而是由重大题材在国民精神塑造中的特殊作用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历史尤其近现代史的特殊的诉求所决定的。中国的历史与文明都比较特殊,它虽然晚于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却比它们要长寿得多,至今绵延不绝,祖宗发明的文字我们仍在用,而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却早已成为化石。我去埃及时,曾寻找创造埃及文明的“法老人”,结果一无所获。事实上,创造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也包括希腊文明)的民族早已不知所踪,生活在这几大文明区域的现代人,与古老的文明没有太多的关系。在埃及,我曾调侃开罗大学的一位教授:你站在伟大的埃及文物面前有民族自豪感吗?他沉默不语。与中华文明这一人类历史上唯一完整的活态文明相比较,我们不觉得美术创作欠账太多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搞“中华文明重大题材创作工程”的原因。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救亡与启蒙的道路上前仆后继,以数千万同胞与先驱的生命铺就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道路。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样的立国之战,中华民族能真正站起来吗?作为中国艺术家,难道不应该书写这样的历史吗?要知道,在图像中构建起来的史诗,不仅能让一个民族对抗遗忘,也能让后人们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当代中国需不需要重大题材创作,更在于如何搞好重大题材创作,如何将史实转化为史诗,搞出史诗级的作品来。从这个角度看,形势就不容乐观了。在一次研讨会上,邵大箴先生问我,“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多少作品能留传下来?我回答:不到10%。邵先生认为我太苛刻了,但回头来看,情况比我估计的还要差。可以说,各类问题比比皆是,比如“摆拍”“画照片”“简单再现”“连环画风”“精神失血”等。原因何在呢?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艺术家们对重大题材创作规律缺乏起码的认识。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重大题材创作从文本撰写阶段就争论不断。围绕对历史现象、事件、人物的认知与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批评家、艺术家各执一词,一度形成互怼的局面。归结起来,所争论的问题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所谓“正史”之外的民间史、民俗史以及欧美汉学家对中国史的研究成果能否进入选题?社科院历史所所拟定的文本基本坚持“正史”观,即便“春节”“中秋节”这样的选题也一概排斥,更不用说“丝绸之路”这类由欧美学者所命名的文化现象与事件了;其二,非视觉化的政策、法令等能否进入选题?艺术家当然反对,因为作品毕竟不是图解政策的工具,但历史学家们坚持。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认知上有很大的错位,按历史学家的意思,重大题材创作差不多就是图解历史,而艺术家则认为,重大题材创作本质上就是艺术创作,创作的语言美学水平决定着创作的成败。
在几项重大题材创作工程的进展中,我一直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当代美术家有无能力担当重大题材创作?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信仰与技术。据我所知,许多美术家是把“重大题材”当作“活”来干的。作为创作主体,他们与题材、内容之间缺乏最基本的情感和最起码的信仰——这就是导致作品精神失血、情感苍白、形象干瘪、叙事乏味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作品,如何作为精神的道场?如何感化大众?如何美育社会?除了在博物馆的仓库中睡大觉外,还能有什么用呢?
技术层面的问题亦有二:一是在传统写实主义领域,存在着普遍的技术退化现象。正如靳尚谊先生所说:一些美术家连基本的造型问题都未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对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媒介、新材料、新技术、新形态、新方法,美术家们一脸的懵懂,几近无知,当然也无法运用它来从事创作。
尽管如此,我还是抱有某种幻想,希望艺术家们能借助于重大题材的力量,来完成一次语言美学和形态的创新。毕竟,历史只有借助于具有创造力美学形式才能真正返回当代现场,而作品也只有通过语言的创新才能撬开历史之门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关注我们,及时获取后续每场活动信息!

留言
留言已提交
经审后可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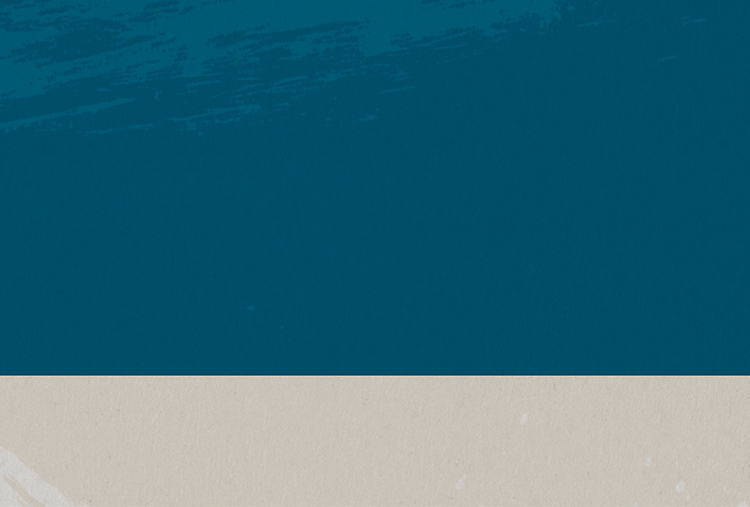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