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谈》(二)
2020-11-02

(二)何为“历史画”?
前面说过,所谓“重大题材创作”即西方艺术史上的“历史画”。从辞源学上讲,“历史画”一词源于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Historia”,指的是“故事性绘画”。“历史画”概念的起源,大约在文艺复兴的早期,至盛期则完全形成。意大利绘画至15世纪,已在透视学、光影学、解剖学、色彩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视觉修辞学语言体系,已具有表现宗教、神话、文学故事、历史事件和非凡人物等重大题材的能力。对文艺复兴的艺术家而言,语言能力的获得带来了革命性的转折:他们不仅能像人文主义学者那样,自由地运用视觉修辞学语言来组织画面,通过得体的方式,将人物与人物、人物与背景组合为和谐统一的关系,完成作品的整体性叙事,将艺术家的手艺与人文学者的智性完美地融为一体,而且,也由此摆脱了下层工匠的身份,扮演与人文主义学者同样的角色。阿尔贝蒂、达芬奇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助产师,他们从理论上明确地把绘画、雕刻从手工行业提升到“高级艺术”的层次。在《论绘画》(1436年)中,阿尔贝蒂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历史画是最高贵的绘画类型:“画家最伟大的事业是历史画”,“画家最伟大的事业是处理某种具有纪念碑意义的题材。”

文艺复兴之后,“历史画”创作在欧洲各大艺术院校中是最高级的专业,课程也最为复杂。让人扼腕的是,现代艺术兴起后,这一专业衰落得很快。20多年前,我去列宾美术学院、苏里柯夫美术学院访问时,特别想观摩一下他们的“历史画创作”课,但结果很令人失望,整体水平令人难以恭维。在古老的教室内,遥想一下列宾、苏里柯夫的背影,竟然生出了几分凄凉感。
谈到文艺复兴“历史画”概念的形成,我有一个很奇妙的感受:从阿西西小镇教堂的乔托的《圣经》故事壁画,到芬奇镇的达芬奇博物馆,隐约地暗含着“历史画”诞生的轨迹。在乔托的壁画面前,我的一个直接感受是,乔托已将《圣经》故事演绎得非常完美了,尤其是隐喻手法运用得十分纯熟。但意大利艺术家并不满足于此,在人文主义进程的推动下,他们自创了一套以科学为基础的古典写实主义体系,并让现实社会及人世俗的生活进入画面,在人文主义与神性并存的新格局中,完成了“历史画”的定位。在达芬奇博物馆众多的科学发明中,我看到的不是一件件充满科学创造力的器物,而是这样的人文盛景: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历史画”正在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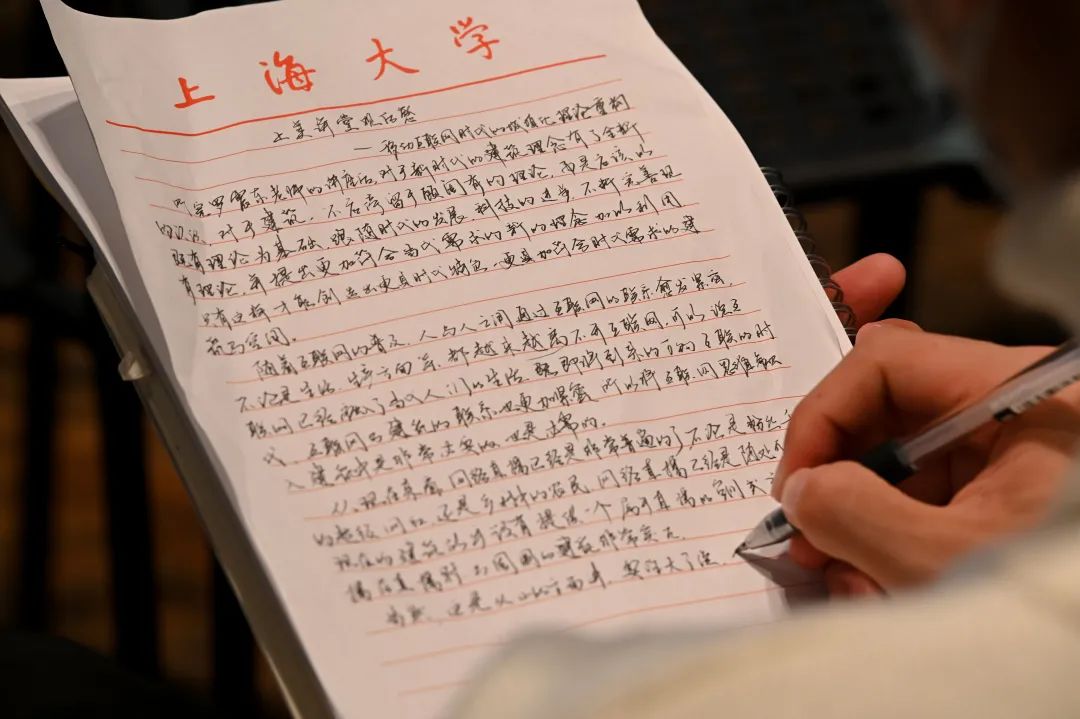
中国的“历史画”古称“故实画”,其发端可上溯至先秦时期。“故实”一词,最早可见于《国语∙周语上》:“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至于“故实画”的功能,谢赫说的很明确:“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也就是说,所谓“故实画”,就是一部关于政治、历史、人文的教科书,所以张彦远将其提升至与“六籍同功”的高度。文人画成为中国绘画主体之前,中国是一个“故实画”大国,且名作迭出。两宋以前,在“故实画”领域,还真找不到能与中国比肩的国家。此时,西方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挣扎,画了1000年的祭坛画,也未能搞出一套完整的叙事方式。文人画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美术开始着意于精神体系的打造,无心过问时事与历史,“故实画”便流落于民间,或被宫廷私藏。14、15世纪,东西方美术格局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当文人画在精神上高蹈远引时,西方则迎来了历史画的黄金时期,有关宗教、神话、政治、时事、世俗生活的叙事,潮流般地湧来,这一湧就是500年。读史可以明智,我说这段话,不是比较中西方艺术的孰优孰劣,而是想从中西方传统中寻找“何为历史画”这一问题的答案。

那么,何为“历史画”?
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回答何为“历史”?
我的回答很简单,历史就是在科学已获知的实证之上,依循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框架,对人类曾经的存在所进行的话语建构。从本体上讲,它就是已故的人类活动与事件的语言编码与叙事。
历史画属于历史叙事范畴。作为一种以图像再构历史实在的艺术创作方式,它拥有历史叙事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它以历史研究文本、历史遗存所提供的“历史真实”为起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学式的写作,一种依赖于想象和虚构的审美图像塑造活动。质言之,它永远徘徊于历史实在与审美话语、“真实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之间,既是“科学的”历史编述,又是“诗学的”历史编述。
这就是我对“历史画”性质的描述,下面,我们进一步探讨“历史画”的本体。
作为艺术家所创作的叙事性图像,历史画通过文献取舍、图像结构、空间处理、人物塑造和历史氛围营构等修辞手法,远远超越了历史文本,超越了历史事件的编年性记述。其关键之处在于,历史画图像不仅试图完成对历史事件所拥有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描述,而且更为重要的,它还表现出对历史事件的整体性观照及阐释的癖好,正是基于这一癖好,使得历史画能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建构出某种历史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由此形成画面的主题。换言之,艺术家以图像创造为中心的叙事过程,本质上就是历史观、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历史画由史实升华为史诗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画图像在语言叙述层面上已完全实体化,形成了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叙述实体”。什么是“叙述实体”?简单地讲,“叙述实体”,就是艺术家对已消逝的历史实在的赋形,使之从历史混沌中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叙事性语言体系。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叙述实体”是艺术家召唤历史实在重新出场的形式,而非历史实在本身。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历史画创作中一个流行的观点:“真实地再现历史”。
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画本体,我略举几例。
《雅典学院》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品,它是拉斐尔1510至1511年为梵蒂冈宫所创作的大型壁画。其上共描绘了11组群57位以古希腊为中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著名人物。站在原作面前,领略其画面的那一刻,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析一下拉斐尔卓越的写实技巧,赞叹一下拉斐尔上帝般把控宏大结构的能力,而是一下子就进入了巨人们的行列,仰视他们的表情,聆听他们的激辩,甚至会观察到他们不易察觉的小动作。比如,一位老人隐伏在毕达哥拉斯的背后,偷偷地抄写他正在演算的公式。徘徊在巨人的沉思、争论、交谈、漫步、计算、研究状态中,会逐渐感受到画面的奥秘所在,那就是,拉斐尔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亚历山大大帝、伊壁鸠鲁、圣诺克利特斯、欧几里得、托勒密、拜火教主琐罗亚斯德、赫拉克利特、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等巨人的讨论与激辩之间,重建了希腊文明精神,揭示了欧洲文明起源的内在逻辑及轴心价值。在拉斐尔那里,画笔就是点“历史”成“当下”的魔杖——他以其天才般的想象重构了雅典学院的盛景,让这一消逝的“历史实在”在“叙事实体”中幽灵般地返回。领略《雅典学院》良久,我虽然意识到这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并非柏拉图的雅典学院,但我还是信以为真了,仿佛历史就是如此。

另一幅大家所熟知的作品是苏里柯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在这幅作品中,苏里柯夫准确地诠释了历史画的意义——不是对历史事件简单而忠实的描述,而是以新历史观为核心所进行的图像再构。近卫军临刑的实际地方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村,之所以被移置于红场上,完全取决于苏里柯夫灵光一现的虚构能力。苏里柯夫回忆到:“某天我走过红场时,周围没有一个人,我站在离宣谕台不远的地方盯着圣瓦西里大教堂的轮廓陷入沉思,突然眼前清晰地浮现出近卫军临刑的场面……”。在苏里柯夫的意识中,红场的建筑物犹如“有血气”的人,远比那个偏远的村子更能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以红场为背景,苏里柯夫在画面上铺展开不同人物命运与情感的叙事:近卫军高傲的不屑、彼得大帝毫无怜悯的冷峻,家属们近乎哀嚎的哭泣、旁观者的冷漠与消沉……在呜咽低沉的画面的旋律中,苏里柯夫揭示了悲剧的根源所在:双方的冲突是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的,因而无可避免。画面上摇曳的烛光与黎明日光的相互交替,或许正隐喻着俄罗斯民族前行的历史必然性。
接着这两个例子,我再借用安克斯密特的另一个概念——“历史表现”,来进一步说明历史画的性质。
“表现(representation)”一词从构词上即可看出使不在场者再度(re)呈现(present)之义。一般而言,表现理论分为“相似论”和“替代论”,安氏弃前用后,在他看来,可以通过某一不在场者的替代物而令其“再度呈现”——原本的事物不在了,另外之物被给出以替代它。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用史学补偿了本身不在场的过去。在这里,历史表现对被表现的过去的替代性、无间性是建立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即“表现与被表现者在本体论上的地位是相同的”。在历史表现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对历史表现的依赖:对当代人来讲,作为曾经存在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历史表现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历史实在的替身——在精神层面上尤其如此。总而言之,只有在历史表现中,历史才得以存在。基于此,历史画作为历史表现的方式,亦是历史实在的存在方式。

陈逸飞、魏景山1977年创作的《蒋家王朝的覆灭》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历史画之一。为了重构这一场景,陈逸飞请雕塑家做了若干场景雕塑,从不同角度观察,终于找到最佳的构图方式——以鸟瞰的角度结构画面,极大地扩展画面的视野,让事件的叙事与前后景观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充分展开;同时,陈逸飞还邀请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化妆表演冲上总统府时的情景,从中找到了人物组合的最具张力的结构和运动旋律。如果将这幅作品与当时的影像资料相比较,会发现两者差距非常之大。这说明什么?说明历史画创作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印证历史事件,而是以“历史表现”的方式重构事件与人物,在象征的层面上揭示事件本身所体现出的历史规律,由此到达历史反思的高度。
在这里,我要特别申明的是,明确叙述实体的本体论价值,强调历史表现理论的意义,并非彻底斩断历史画图像与过去实在之间的认识论链条。事实上,由历史研究文本、历史遗迹、考古学成果等所组成的科学实证体系,一直是历史画创作不可或缺的基石。通常意义上,我们将其称之为“历史的真实”。同时,另一方面,还有在历史画叙事实体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更高的真实,即“艺术的真实”。何为“艺术的真实”?我的解释是:对历史规律及意义的哲理式观照所表现出的历史真实性,是在作品的审美叙事中完成的,因而,可称之为“艺术的真实”。
我并不想对历史画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想结合前面所讲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小结: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历史画与历史研究文本之间并非简单的图像对文字的转译关系,也不是历史遗迹、考古学细节陈述的总和,更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忠实描绘与写实性再现,与此相反的是,历史画的性质应明确地表述为:以科学实证为基础,通过特有的阐释模式、修辞策略和审美叙事,将历史置于历史表现层面,在那里建构历史的意识形态和哲学图景。唯如此,历史事件、重大题材才能由史实转化史诗,历史画才能成为烛照过去并使之呈现与返场的隐喻式澄明——从根本上讲,建构民族的精神史诗不仅涵盖了历史画的意识形态,也是其终极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作为对历史实在的审美编叙,历史画创作要同时面对三重压力:科学实证、意识形态建构、审美图像塑造。我以为,这就是重大题材创作艰深而伟大的原因。

关注我们,及时获取后续每场活动信息!

留言
留言已提交
经审后可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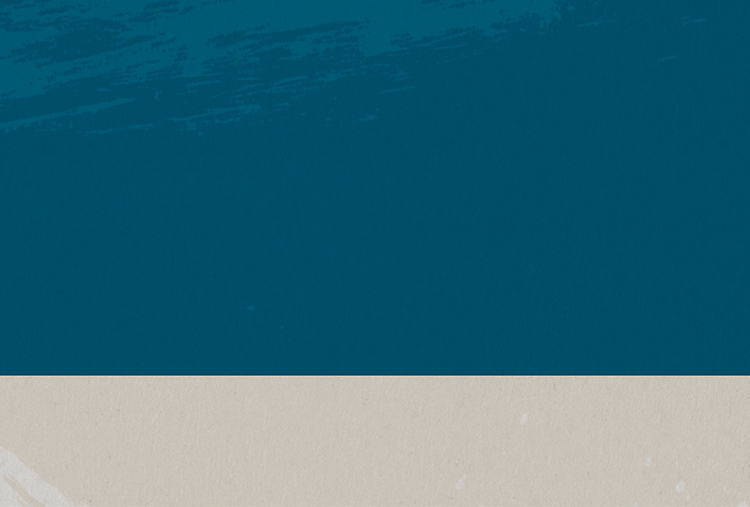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