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谈》(三)
2020-11-02

(三)历史画创作
我向来主张,重大题材创作一定要理论先行,不在理论上弄懂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性质,就容易把重大题材画成连环画。那么,理论上有所认识后,如何将其转化为创作实践,就成为重大题材创作成败的关键。
先讨论一下什么是重大题材。我给出的答案是:只有那些体现出历史发展态势及规律,呈现出民族精神特质的事件、现象、观念、人物及景观,才能称得上重大题材,共约九个方面:
1、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董希文《开国大典》、刘开渠等《人民英雄纪念碑》)。
2、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或群体(阎立本《历代帝王图》、靳尚谊《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朝闻《毛泽东侧面浮雕像》、冯远《思想者》、曾成钢《霍去病》)。
3、具有历史影响力的现象(阎立本《步辇图》、提奥∙埃舍图《破碎的地图》(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作品))。
4、推动历史前进并深植于民族记忆中的观念或信念(唐勇力《新中国的诞生》、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5、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风俗及礼仪。(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6、体现时代特征的日常生活场景(周昉《簪花仕女图》、老勃鲁盖尔《农民之舞》)。
7、具有政治、社会内涵及历史象征性的风景和景观(列维坦《弗拉基米尔之路》、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
8、当下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籍里柯《美杜莎之筏》、《太阳与海》(58届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作品))。
9、神话与传说(马王堆1号墓帛画、波提切利《维纳斯诞生》)。

近些年来,国家级的重大题材创作都以“工程”来命名,有学者便跳出来反对“工程”的定性,理由是会影响艺术家独立创作的自由。的确,这里确实存在如何处理好个人意志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国家在政治实体层面上所形成的具有权威性的精神形态,它是国家发展的基本价值框架,或隐或显地规约着时代的走向与民族的精神生活。对重大题材创作而言,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重大历史题材的选定及相应的阐释;2.国家意识形态在作品中的呈现;3.作品完成后相应的政治、社会、宗教、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审查。当然,国家意识形态也是与时俱进的,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意识形态对历史画创作的要求就经历了“人民革命”“阶级性”“人民性”“民族国家”“民族精神气质”等数度文化立场与主题的转换。在创作实践中,认同、理解并在作品中呈现国家意识形态是艺术家承担创作任务的基本要求。换言之,艺术家个人意志主动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是历史画创作的前提。当然,艺术家并非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历史画也并非历史宣传画。在历史画创作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与历史事件的表现之间,为艺术家的个人意志与创作自由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历史画依赖于艺术家对历史事件的“猜测”与想象。所以,历史画在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必然地表现出艺术家的个人意志——这是历史画往往主题鲜明而又寓意复杂,具有复调性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从项目策划、题材选定、文本阐释、主题确立到草图审定乃至作品的完成,历史画庞大的创作结构就是一个共谋性的“工程”结构。其中,作为赞助人、委托人的国家,文化管理机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及艺术理论家,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承担了不同的职责。比如,在“中华文明重大题材创作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冯远主席多次带队去艺术家工作室审稿、讨论,并亲自撰写修改意见。“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也是如此,每幅作品差不多都是管理者、批评家、理论家与作者共谋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断言,历史画与其说是艺术家的苦心孤诣之作,不如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美学风格亦由此呈现出集体主义美学、国家主义美学的特征。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重大题材创作中几个紧要的环节。
在我看来,历史画创作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以何种性质的叙事方式将历史事件转换为史诗性的视觉图像。通常而言,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艺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可大体分为三个类型:史传性、史诗性和演义性。史传性接近于德国史学家兰克所说的“如实直书”。这种叙事方式讲究考据,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力图还原真实,这是编年体史学家常用的叙述方法;史诗性居于史学家与艺术家的态度之间,是历史与艺术、事件与虚构、文献与想象相结合的叙述方法;演义性则更多地听命于艺术家的虚构,近于纯粹的文学、美术创作。从历史画的创作规律来看,历史画多采用史诗性叙事——历史上,那些标志着艺术史高度的伟大历史画作品,其价值与美学魅力,均来自于史诗性叙述。

有趣的是,在“中华文明重大题材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等项目的研讨与审稿中,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似乎不买史诗性叙事的帐,他们更喜欢“笔笔有来处”的史传体。在一次审稿中,考古学家孙机指着一幅草图批评道:这件作品至少有三百个错误。孙机先生的话当然是激愤之言,但也提出了历史画创作采用何种叙事方法这一关键性问题。按照孙机等考古学家的意见,历史画创作将被严格限制在考古材料和事件的真实性层面,最大程度地剔除虚构与想象。很显然,孙机先生不太清楚历史画创作的性质与规律,混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在历史上,有以史传体进行创作的例子,但那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法国大革命期间,由雅各宾派出资,大卫负责创作颂扬大革命的油画《网球厅宣誓》。出于对大革命的赤诚,大卫力图以描绘“真实历史”的方式进行创作,想忠实地再现这一盛大的革命图景。这个想法虽值得尊重,但却与历史画的叙事方式相抵牾,致使他最终未能完成这件作品。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克劳批评道,这条创作道路实际上并非历史画的新出路,而是一条死胡同。
史诗性的叙事方式落实于画面结构,又可分为“时间中的叙事性”和“空间中的表现性”两种方式。前者为情节性的,后者为非情节性的。情节性绘画,英文作“narrative painting”,通常用来叙述某一具体事件。其策略是通过描绘特定时空中某一事件最具包孕性的瞬间,或有意味的刹那,来表现已发生的事或即将发生的事。为了表现这一瞬间,画家往往要像戏剧导演那样来调度画面,充分利用光影、空间、造型等修辞学手段,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秩序与情节要求,来处理画面人物之间的关系,由此达到叙事的目的。这种叙事方式成就于意大利学院传统,通过法国、俄国学院传统而传入中国,成为新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叙事方式。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新中国重大题材创作的叙事方法主要取自于法、俄,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是一个“故事性绘画”的大国,其传统美术拥有丰厚的叙事方式与类型。这一点,在上一节有所提及,下一节谈到重大题材创作的语言形态与风格时,还要讨论。在此仅举一个例子,比如《韩熙载夜宴图》。
这件作品的背景大家都了解,南唐画家顾闳中奉君主李煜之命,以图绘的方式表现三朝元老韩熙载的夜生活。浏览画卷,如果你能领略一二,便知顾闳中是一个真正的讲故事的高手。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顾闳中就将整个叙事分为显、隐两条线,显与隐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叙事结构。显的叙事线索由听乐、欢舞、休息、吹奏、送客五种场景构成,隐的线索也就是画面的心理叙事:每个人不同的体态、动作、情状、神貌乃至身份,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心理场域。两种叙事在“有形”“无形”之间不断交汇、碰撞、互击,形成了画面的“复调”:奢靡与消沉、纵乐与隐忧、热烈与漠然。我认为,顾闳中是心怀天下的文人,而不仅仅是画院的画师。他奉献给李煜的,与其说是一幅画,不如说是一个寓言。将奢靡呈现于灿烂中,所隐喻的正是国家的危机,但李煜似乎没有领会此图的深意,其后的亡国便在情理之中了。大约在2006年,台湾的戏剧制作人将《韩熙载夜宴图》搬上了舞台,并在故宫的大殿前做了一场演出。是夜,秋风浩荡,花树滉漾,宫阙巍峨。那件无声的史诗,此刻竟声色并茂。身置其中,聆听雅乐,恍然与千年前的夜宴相遇,而故宫与“夜宴”交叠而成的意象,让我再次回味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存亡之道。我想,这大概就是史诗的魅力。

再来看另一种叙事方式:“空间中的表现性”。这种叙事方式多用来叙述整体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或观念。在这种叙事方式中,人物、事件超越时间、情节的制约,以某种观念为核心而被置于空间性的结构中。其形态多样,既包括以超时空结构为基础,对整体性的历史事件作综合性的叙述;亦包括以象征主义手法来表达某种哲理与观念;同时,也包括以抽象、表现的方法与形态来呈现历史事件的整体境况与内在结构。象征、寓意等手法的广泛运用,让这个叙事类型的历史画好像披上了寓意画的外衣。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克里姆特的《死神与生命》、冯远的《思想者》、西盖罗斯的《新民主》、提奥∙埃舍图的《破碎的地图》、安妮∙伊姆霍夫的《浮士德》,都是这种叙事方式的极好例证。《自由引导人民》虽取材于1830年七月革命中的具体事件与人物,但其女主角克拉拉·莱辛却在德拉克罗瓦的笔下圣化为引导人民的自由女神,从而让这张作品由“时间中的叙事性”转换为“空间中的表现性”。《格尔尼卡》在马德里索菲亚王妃美术馆的一个专厅中陈列。这张作品以黑、白、灰三色与象征手法营造出的气氛,接近于死亡。时空在这张作品面前仿佛被冻结了,所有的观者冥想般地陷入了宗教性的沉思。我在现场的感觉的确如此:它所捕获的,不仅是观者视觉,还有灵魂。

在历史画创作实践中,无论采用哪一种叙述方式,其主题都必须建立在三个支点——科学实证、象征性画面结构和具有心理自传性质的人物形象——之上。
科学实证之下的所有考古学细节与历史文本乃是历史画创作的起点与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细节决定了历史画的成败。所以,艺术家需理解这样的铁律:历史画创作往往从做学问开始。艺术家在历史文献分析,考古学细节探究,以及对环境、道具的收集与氛围的感受中所获得的“历史真实”,是历史画的第一个层级的真实。在这方面,日复一日在开封市井中研究民俗、建筑与各色人物的张择端、潜入韩熙载府邸收集素材的顾闳中、主动借鉴历史与考古学成果的苏里柯夫,都是极好的榜样。近些年重大题材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数多原因来自于艺术家未能潜心学问而导致的无知。比如,画张骞出使西域,所乘坐骑已有马蹬,实际上西汉时马蹬还未发明。“茶马古道”的画面背景、道具,与实际情形也相差很远。总之,这类毛病很多。如果艺术家将自己的想象与虚构能力建立在这样的“毛病”之上,无疑于筑坝于沙,难以成立。我建议,艺术家们在从事历史画创作时,要记住德拉克罗瓦说的那句话:由真实历史的激发和启示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成为创作一件艺术作品的前提。
在创作实践中,如何围绕历史观与主题的建构,凭借想象与虚构能力,在审美叙事层面上,塑造出具有历史象征性的画面结构,成为历史画创作的核心要义。在这里,空间、时间均超越了历史事件所固有的物理性限制,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而形成自在自为的结构。与考古学、历史文本所提供的“历史真实”相比,因象征性画面结构隐喻着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精神意向,所以,它是更典型、更概括的真实——一种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更高级别的真实,也即“艺术的真实”。它完全可以替代或补偿已逝去的历史实在,与历史实在具有等值的本体论价值。在上节有关历史画本体论的讨论中,我们已谈过这个问题。
准确地讲,一切伟大历史画作品中的空间都并非现实的物理空间。艺术家创作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像阿尔贝蒂所说的那样,是“第二个上帝”重塑时空的活动。苏里柯夫一直在寻求与题材、主题、事件及人物相符合的具有精神象征性的空间;与此同时,他作品中的时间也超越了物理限制,是具有创造性的、以人的生命为单位而加以衡量的历史时间。唐勇力的《新中国的诞生》也是这方面的范例。中国红基调、金碧辉煌的传统纹样、汉白玉、巨大的灯笼、飞翔的和平鸽、游观性与装饰化的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走向新生的精神符号。
历史画叙事的另一个支点也极为重要,那就是塑造具有心理自传的人物形象与性格,着力表现人物在历史情境中的心理状态。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塑造具有心理自传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历史阐释的必要维度,也不仅仅是还原、表现历史人物的方法,同时,更重要的,它还是历史画到达民族精神史诗高度的必要途径。可以肯定地讲,人物心理阐释所达到的深度与生动性,决定了史诗性叙事的高度。
俄罗斯历史画创作之所以得到欧洲主流艺术史界的承认,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心理阐释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宾、苏里柯夫的历史画,在汲取“历史肖像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状态这一优长的基础上,将画面人物不同性格演绎为复杂的心理学图谱,其“复调”所形成的多声部对话,成为人们领略俄罗斯民族性格底色与末世关怀意识的最好方式。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人们很难抵抗列宾的《伊凡雷帝》那雷霆万钧般的视觉压力。伊凡雷帝双眼中的惊恐、悔恨及自责,与儿子眼中的宽恕、平静、无力及绝望相互交织,迸发出了勾魂夺魄般的力量。在《拒绝忏悔》中,列宾以牛氓蔑视死神的表情,准确地诠释了革命者的真正含义。读了这些作品,人们或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列宾、苏里柯夫与其说是历史画画家,不如说是心理学家。
通过以上三个环节,历史画才能在隐喻层面上呈现出历史哲学的图景,并在那里完成民族精神史诗的宏大建构。

关注我们,及时获取后续每场活动信息!

留言
留言已提交
经审后可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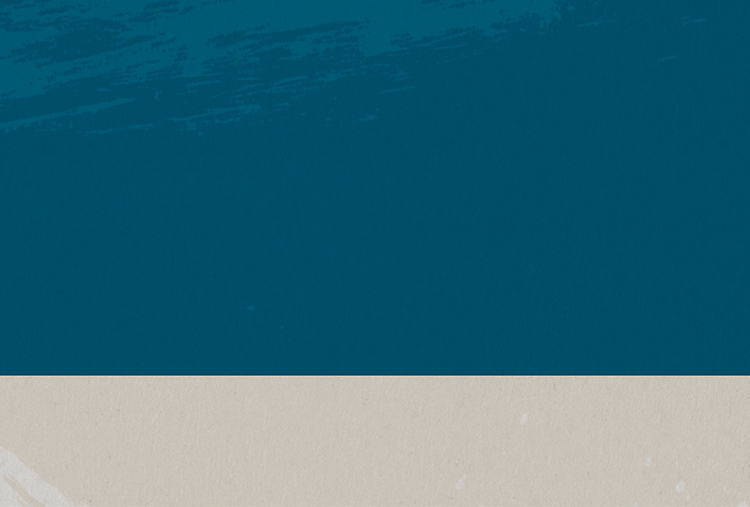




留言